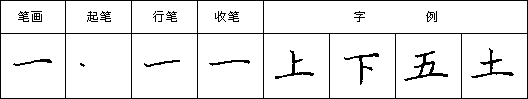二、徽派篆刻的發展(1644 ―1848)
1.徽州考據學對篆刻藝術的影響
文人篆刻由對篆法的研究,轉而對刻法的重視,繼又講究篆刻合一,融筆意于刀法之中。有明一代文人篆刻藝術的發展,就是在這種螺旋式的發展中,不斷升華。
文人自有文人的優雅,操刀刻石,像李流芳、歸昌世、王志堅輩“每三人相對,樽酒在左、印床在右,遇所賞連舉數大白絕叫不已”,是極為痛快的。后來“三人為世故所驅,俯首干時”,①不再有刻印時的那種激情和沖動。篆刻,由于有“刻”這樣一種匠式操作過程在其中,似乎總不那么雅,于是文人自嘲式地稱篆刻為“雕蟲小技”。但又總是抵擋不住方寸之間的那種無窮的藝術魅力,便想出點子說,篆刻的落腳點是“篆”而非“刻”,是學問而非技藝。明末清初之際,當“刻”的技法被文人們普遍掌握之后,大家對“字”的重視特別顯現出來。對文字淵源流變、金文刻石的研究,成為篆刻理論和篆刻藝術實踐的重點。
清代徽州考據學的興盛,代表了清代學術的最高成就。考據學雖不為篆刻而起,但它對金石文字的考證研究,對篆刻藝術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徽州學者做學問,主張重史實依據,解經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注重考據。朱熹曾說:
學者觀書,必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徑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一般,方能玩味。②
明萬歷時期,徽州的文人曾撰寫了一批文字方面的著作,可視為考據學的發端。歙縣吳元滿撰《六書正義》12卷、《六書總要》15卷、《六書?源直音》2卷、《諧聲指南》1卷,凌立撰《字鏡》4卷,休寧詹景鳳撰《字苑》,婺源游遜撰《字林便覽》4卷。考據家鉆研字學,是為研讀經史,篆刻家鉆研字學是為辨明書體,兩者雖有側重,但并不矛盾。吳元滿同篆刻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前面已經談到。詹景鳳雖沒有篆刻方面的記載,但他本人是明代著名的書畫家和書畫鑒賞家,其孫詹吉工篆刻,有秦漢體裁,想必詹景鳳也不會疏于篆刻。明末清初歙縣巖鎮人程邃,“能識奇字,釋焦山古鼎銘,辨其可識者七八十字”。①得力于對文字學的深厚學養,程邃借鑒鐘鼎彝器款識和刻石的文字,打破前人所謂大小篆不能混用的清規戒律,“合款識錄(按:青銅器銘文)大小篆為一,以離奇錯落行之”,②開后世印外求印之先河。明末至清中葉,徽州出現了不少金石文字輯錄的著作。主要有江紹前《金石錄》20卷,許楚《金石錄》,吳玉?《金石文存》,方成培《金華金石文字記》1卷,巴樹谷《向藻閣金石文字記》1卷,吳穎芳《金石文釋》6卷等。
雖有金石錄,如不識金石上的文字,亦為枉然。乾隆以前,印學界對印章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的嬗遞演變、繆篆與正篆的區別、官和私印章名稱考訂等方面,對古文字的研究水平并不高,更談不上借鑒金石以提高篆刻藝術水平。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董洵作《多野齋印說》,談到古璽時說:
朱文小印,文多不識,而章法、篆法極奇古,相傳為秦印,朱修能定為三代印。白文有邊者,文亦奇古難識,末一字或謂是“汊”。按:汊,諾葉切,音捻。《博雅》云:正也。《五音集韻》云:小箱也。然則,何所取義?嘗取數印審視,左不盡是“金”,右不盡是“爾”,恐未必然。相傳為西漢印,二者竊疑之。
董洵因不懂古文字,無法考證清楚古汊,導致“汊”字的讀音和釋義的錯誤。考據學家由于精通經史,對古文字觸類旁通,往往發印學家所未能發。
清初歙人黃生撰《字詁》,鉆研文字聲義之奧。又撰《義府》,詳細考論經、史、子、集,辨證精確,開徽州考據學先河。黃生本人也是一個篆刻家,其子黃呂幼時即受庭訓,印作遒勁蒼秀,有秦漢遺風,為汪啟淑刻印多方,被收入《飛鴻堂印譜》。比黃生稍晚的婺源人汪紱,專意以考據治經,涉獵極廣,凡樂律、天文、地理、兵制、繪畫、篆刻,無所不通。考據學家汪肇龍,少時家貧,13歲進學,初習篆刻,因篆刻而通六書。后來與戴震同學于江永,專治經學。于《爾雅》、《說文》諸小學書及水經、地理、步算、音韻、器物等諸書無不博覽涉獵,師友均服其精。游京師,觀太學石鼓,于是摹而注釋之,著有《石鼓文考》。至于尊彝、鐘鼎等古篆、云鳥、蝌蚪文,寓目輒能辨析。曾為汪啟淑刻印多方,收入《飛鴻堂印譜》,與程邃、巴慰祖、胡唐齊名,為“歙四家”之一。
著名的徽州考據學代表人物程瑤田,著有專門的解字著作――《解字小記》。正因為他有著深厚的文字學功底,在為《看篆樓古銅印譜》作序時,對古汊印文中的“汊”與“私汊”進行了詳細考證:
芝山乃復指一事,曰“王氏之汊”,以謂余曰:若知“汊”為“璽”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昔余每見銅章,有曰“某汊”者,嘗疑之,因檢《汗簡》有之,曰“ 蝗 ”字也。箝蝗之字,無當于印章。今自芝山言之,是亦“璽”字耳。《說文》璽從土,曰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然則本從土,以玉為之則從玉,以金為之或又從金也。然據《說文》:“璽”,專屬之王者,而蔡邕《獨斷》,則以“璽”為古者尊卑共之,秦、漢以來,惟至尊稱“璽”,皇帝六璽以紫泥封之。劉熙之釋“印”字,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余據二書,以為“璽”,從土者從封省也。既尊卑共之,則王者守土之說非也。今曰“王氏之汊”,則卑者稱“璽”之驗也。于是復相與披譜,見曰“?汊”,又見有“?汊爾”者,又見有“?”者,芝山曰:是何也?余曰:此皆“私璽”二字也。私璽者,卑者之璽,所謂尊卑共之者也。“璽”但用“汊”者,古文省也。
程瑤田在這里以古印考證研究印史,確認璽為秦以前印章,并認為是尊卑共之。又從“私”的考證,確認“私汊”是當時的“卑者之璽”。程瑤田以他精湛的文字學功底,解決了董洵沒有解決的古璽問題。程瑤田也是一位頗有成就的篆刻家,為汪啟淑刻過印章,被收入《飛鴻堂印譜》。
由于對先秦文字不認識,篆刻家們在用大篆入印,用古璽形式創作時,往往不得要領,影響了印章的審美意趣。考據學家的介入,先秦文字開始被人們所認識,也為人們認識古璽形式美掃除了障礙,使篆刻藝術創作進入一個新的天地。
清初至清中葉徽州考據學家介入印學領域及徽州印人印外求印的藝術實踐,帶動了徽州篆刻藝術的興旺,產生出程邃、吳?、汪肇龍、巴慰祖、胡唐、項懷述等一大批篆刻名家。而且影響波及整個印壇,如丁敬有《武林金石錄》,張燕昌有《金石契》、《石鼓文考釋》等。鄧石如得到畢蘭泉家藏舊拓《瘞鶴銘》,刻“意與古會”印,跋曰:
向之徘徊其下摩挲而不得者,今在幾案間也;向之心悅而神慕者,今紱若若而綬累累在襟袖間也。喜悅之情,溢于言表。丁敬、張燕昌、鄧石如后來都成了篆刻大家。金石與篆刻也結下了不解之緣,一度金石也似乎成為篆刻的代名詞。
2.徽商對篆刻藝術的支持。
從明代中葉至清代中葉的三百年間,是徽州商業經濟最為發達的時期,同時也是徽派篆刻發展最興盛的階段。因徽商的富裕,人們追求風雅,人文風氣濃厚。商人利用自己手中的金錢,大量收藏各種古玩字畫,為藝術家們借鑒古人的創作經驗提供了直接觀賞臨摹的機會。
明嘉靖時期著名墨商羅龍文,家中富有,收藏了大量的古董、法書、名畫、印章,其子羅南斗又獨愛印章,精鑒賞,亦能刻。羅龍文曾為嚴世藩幕僚,與嚴世藩同死于西市。家難后,古玩字畫盡皆散佚,惟印章由羅南斗保存未失,后羅南斗借以協助顧從德輯鈐成《集古印譜》行世。羅南斗的后裔羅逸《題羅公權印章冊》稱:家延年好文博古,以父內史畜法書名畫甚富,故得多見往代金石遺文,其工于印章有自矣。內史任俠饒智,佐明胡襄懋平島寇有功,至今人能道之。又嘗仿易水法制墨,堅如石,紋如犀,黑如漆,一螺直萬錢。后坐事見籍,獨古印章存,延年益校其精者梓行之,今云間顧氏印譜、海陽吳氏印譜是也。①清代,徽商收藏更富,“休歙名族,如程氏銅鼓齋、鮑氏安素軒、汪氏涵星研齋、程氏尋樂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書籍、法帖、名墨、佳硯、奇香、珍藥與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屬,每出一物,皆歷來賞鑒家所津津稱道”,①其中自然也有大量的古璽印章。談到徽商對篆刻藝術的支持和貢獻,我們不能不特別要提到汪啟淑。
汪啟淑(1728―1800),字慎儀,號?庵、秀峰,歙縣綿潭人,業鹽于浙,僑寓錢塘。工詩好古,收藏甚富,尤嗜印章,自稱印癖先生。搜羅古璽以及秦、漢迄至元、明歷代印章數萬方,又曾于巨珠上刻作篆文,以補諸品未備。相傳錢梅溪有漢“楊惲”二字銅印,汪啟淑欲得之,錢不許,于是長跪不起,錢不得已,笑而贈之。輯有《集古印存》、《漢銅印原》、《漢銅印叢》、《靜樂居印娛》等印譜20余種。他憑借雄厚的財力,廣泛接交印壇名人,如林皋、吳?、丁敬、黃易、黃呂、張燕昌、吳兆杰、董洵、王轂、汪肇龍、桂馥、程瑤田、汪士慎、潘西鳳等100余人,邀約篆刻印作,先后收集當時知名的篆刻家作品3000余方,因而編輯厘訂,鈐印成《飛鴻堂印譜》5集40卷行世,風行一時,成為乾隆時期印壇名手作品的集中匯展。收錄入《飛鴻堂印譜》印作的作者,汪啟淑又另編著有《飛鴻堂印人傳》(后易名《續印人傳》)8卷,與《飛鴻堂印譜》一同行世。汪啟淑以一人之力,鈐拓眾多的古印譜,又匯輯鈐錄當代人的篆刻作品,為印人借鑒古代優秀作品和了解當代印人風格提供了條件,繁榮了乾嘉時期篆刻藝術創作。汪啟淑雖為徽州人,但他常居杭州,其飛鴻堂作為浙人的聚會場所,客觀上為浙派篆刻的興起起到了促進作用。
對一些貧困的印人,徽商也給予了直接的經濟支持。歙縣人張鈞,字鏡潭,家世力田,然生而好古,“稱貸戚友購覓陳倉、石鼓、禹穴、嶧山諸碑,忘餐廢寢,昕夕研究而討論焉。遂兼工制印,刀法即蒼勁古雅,殆天賦也”。但自身的貧困使他不能安心篆刻藝術。“有邗溝族人某,雄于貲,重其誠實,延佐理財,鏡潭亦藉以少裕”。②由于有同族商人的幫助,張鈞不再為生計發愁,終于能安下心來進行篆刻創作,有《鏡潭印賞》10卷行世。
徽商屬于一個文化修養水平較高的社會階層。他們或“先賈后儒”,或“先儒后賈”,或“亦儒亦賈”。做官不成,亦可弄文,吟詩作畫是儒商的一種表現,篆刻同樣也是商人附庸風雅的一種形式,甚至在商人群體中產生出一些篆刻大家。
羅南斗為徽商后裔自不必說。金一甫“家擁多貲,乃多雅尚,究心篆籀之學”。①在徽州“家擁多貲”者,一般為商家,可以斷定,金一甫是出身商人之家。清初休寧米商汪濤,精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②歙縣人汪芬,字桂巖 ,出身鹽商世家,除習科舉制藝之外,凡詩古文辭亦涉獵,并喜篆刻。乾隆二十一年(1756),汪啟淑“歸綿津掃墓,桂巖過存下榻予齋,朝夕相與討論,時有新意,發人所未發。作詩亦頗清晰。因將大小石數十枚俾刻,并語以考別古文、繆篆。出示所藏古人印譜,而技益進。其印組題跋,亦瀟灑有致”。③歙人黃塤因其父在杭州經營浙鹽,以商籍補博士弟子。“工大小篆、八分書,畫墨菊頗饒幽致,寫蘭竹則又雙管交飛,解悟昔人怒喜行筆之旨。復寄興篆刻,宗蘇嘯民、吳亦步,章法、刀法古樸蒼勁”。④程瑤田也是出身徽商世家,乾隆十年(1745)曾至杭州應商籍試。其子程培在揚州經營鹽業。歙人徐履安為大鹽商徐贊侯的侄孫,“工篆籀,人呼為鐵筆針神”。⑤歙人兩淮鹽業總商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富可敵國,家中收藏甚富,喜延名流,當時的一些篆刻名家均與其有交往,座客常滿,極一時文酒之盛。兄弟子侄輩或商或儒,有的擅長詩文書畫,有的則精工金石篆刻。如江恂“收藏金石書畫,甲于江南”;江昱“工詩文,精于金石”。⑥乾嘉時期歙縣漁梁巴氏經商世家,出了巴廷梅、巴慰祖、巴樹谷、巴樹?、巴光榮四代五位篆刻家。其中巴慰祖從小就愛好刻印,他說:“慰糠秕小生,粗涉篆籀,讀書之暇,鐵筆時操,金石之癖,略同嗜痂。”⑦巴慰祖的外甥胡唐,在舅舅的影響和帶動下,也酷愛篆刻。由于巴慰祖嗜印,二個兒子及孫子、外甥也好印,不能安心經商,以致到了晚年,家道中落,只好為人作書、篆刻自給。雖然經濟上窮了,但篆刻水平卻得到了提高,聲名流溢。巴慰祖、胡唐同時被列入“歙四家”,發揚光大了徽派篆刻藝術。
3.眾多的篆刻創作隊伍
清代印人同明代相比,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文人氣息更濃了。何震、蘇宣、朱簡、汪關、金光先、江?臣純粹是以印人的身份立足于印壇,但清代的印人或為官,或為商,或從醫,或善于詩,或長于畫,或從事經史研究,甚至集儒商醫于一身,熔詩書畫印于一爐,這樣一來從事篆刻創作的人也就更多。特別明末清初是中國畫獨一無二的表現形式――詩文、書法、印章和圖畫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定型階段,故對文人畫家來說不僅畫要畫得好,詩文、書法功底要厚,最好能自己刻印。就是不會刻印,也一定要找篆刻高手為自己刻上幾方精美的印章,為書畫作品增輝。無疑這對篆刻藝術創作促進很大,清初至道光間徽州涌現出100多位印人,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書畫家兼篆刻家,其中程邃、鄭 ?、戴本孝、黃呂、汪士慎不僅在印壇名盛一時,在畫壇更是譽隆天下。項懷述、巴慰祖、胡唐則是書壇大家,項懷述有“八分一字百金酬”之譽,①巴慰祖隸書被稱“有建寧延熹遺意”。②詩、印兩棲的大家有汪炳、汪鎬京、吳?等。
汪炳和程邃跨明清兩代,但他們的篆刻創作活動主要在入清以后,是徽派篆刻確立和發展階段承先啟后的兩位重要代表人物。
汪炳,字虎文,休寧舊墅人。明崇禎時,其父和兄均在北京為官,汪炳生于北京。少時讀書,過目成誦。其兄精篆隸真草四體書法,是以汪炳于書法特有家學。清兵入關以后,全家南遷,移居杭州。見朱簡《印譜》,特別喜愛,于是握刀摹刻,得其意趣。③后來在揚州遇到程邃,談起篆刻,彼此拿出各自的印譜互相求證。程邃對汪炳的篆刻技藝極為嘆服,握著汪炳的手說:“始吾自以為無塒者,今見子,則此事當與子分任之。”汪炳笑著說:“子既以此得名矣,吾又攘其善,吾不為也。”高鏡庭酷嗜程邃的印作后,看到汪炳的印作后,前往拜訪汪炳,抓著汪炳的衣袂說:“幾幾乎交臂而失之,吾從此可無須程子矣。”當時浙中的篆刻名手徐念芝聞其名,見其印,亦拜其為師。從汪炳學的還有吳下揚敏來諸人。
程邃(1607―1692),④字穆倩、朽民,號垢區、青溪、垢道人。歙縣巖鎮人,生于云間。明末歙縣諸生。早年曾入兵部尚書楊廷麟幕中為僚屬,因議論朝政,被流寓白門十余年,剛得解脫,又因議論“馬士英眼多白,必亂天下”而遭迫害,險些喪命。入清后寓居揚州,專以書畫篆刻自娛。博學、多能,工詩善文,書、畫、篆刻均有很深的造詣。繪畫純用枯筆渴墨,干皴中滿含蒼潤,簡單中富含重重變化,在畫界自成一格,是清初畫壇宗師。篆刻朱文仿先秦璽印,以鐘鼎款識入印;白文精探漢法,刀法凝重。清順治時,輯鈐有《程穆倩印藪》行世。施閏章順治十七年(1660)作《程穆倩印藪歌》七古一首:
黃山山人真好奇,性癖膏肓不可治。雕鏤文字壽琬琰,蟲角錯落蟠蛟螭。
苦心愛者有數子,摩挲只字等禹碑。亦如昌黎推作者,險奧不廢樊宗師。
九月邗關木葉下,山人邂逅同僧舍。自言好古非雕蟲,篆籀周秦足方駕。
詰曲迷離多不辨,相逢十人九人詫。可憐古籍秦火焚,存者如縷金石文。
峋嶁鐘鼎盡奇字,恍惚天矯凌浮云。今人能手類刻木,仰唇俯足徒紛紛。
豈若山人眼空六書與八分?驚魂駭目天下聞。噫嘻!山人好古不能長得食,何如歸老黃山三十六峰之南北。赤文綠字藏其間,風雨千年無剝蝕。①程邃又有自輯《印譜》二冊,《中和月刊》第1卷第9期(1940年9月)娛湛老人《印林清話(上)》一文載:
明人程邃字穆倩,號垢道人,性嗜藏印,亦喜雕刻。嘗集印譜冊頁兩本。上冊古印,下冊所治之印,意殆示人以己刻胎息古人。冊尾有鄭板橋 燮題字,為?翁舊藏,曾見于?翁之孫菊曾部郎陶處。菊曾歿后,上冊歸津沽孟伯方手。其下冊由菊曾之子質于海豐吳氏。事閱廿年,不知流轉何許,恐難為延津之合劍矣。
上冊今已不知下落。下冊啟功先生曾見,汪世清先生說,啟功告訴他“程穆倩印譜冊,素冊十開半,分粘印拓357枚。冊頁副頁鄭板橋題二開,冊后副頁鄭板橋題一開半,何子貞題一開。”據說此下冊今存文物研究所。
程邃之子以辛,字萬斯,亦能作印,有《程萬斯印存》行世。王概《山飛泉立堂稿》有《程萬斯印存序》,稱程邃“晚年諸作皆出萬斯手也,惟吳文禧公能區別之”。程邃的兒女親家吳山亦能刻印。吳山之子、程邃女婿吳萬春篆刻步其岳父法,唯刀法稍弱。
明清之際,翻天覆地的朝代更換和社會動亂,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處于下層的文人及藝術家由于強烈的民族意識,不愿為新政權服務,無論其思想意識或生活經歷,都給他們的創作帶來一定的影響。鄭?和吳?的篆刻創作,就是在這種矛盾和貧困中進行的。
鄭?(1633 ―1683),字慕倩,號遺?,歙縣鄭村人。本名? ,入清后移日于左,寓無君之意,以布衣終老山林。工詩善畫,精于篆刻。鄭?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氣節的遺民,在生活極其貧困的情況下,堅持不與官場人士交結,“簪紱中人有愿近昵者,哭拒之,或先避去,雖堅請不出也。饑則以詩畫易米,然以金帛干之則必不與,即或成幅亦毀之。”①所著《拜經齋日記》記載鄭?康熙十一年(1672)至康熙十五年(1676)的生活日記,其中經常談到有關篆刻的情況,如在康熙十一年(1672)四、五、六三個月的日記中記載:
四月廿二……得頌月聯章致于鼎,印章屬之仲云,并至一字托錄姚公詞。
廿七。畫梅竟日。為只承二印章。
五月五日,午晴。薄醉后,步月理連月月句,僅得六章。
七日,雨……為只承懶齋印章。
八日,下郡……過允凝,不值,乃子銘二少款習為篆刻事,出所制相質。
六月五日……篆“大癡”、“云林”、“章候”、“梅壑”諸印章,蓋以饑年少為生發, 亦當慎所施。
七日,寒食……為昭候二章,祀先。
十八日。王卜臣貺香索印章。
十九日。為卜臣印章。
廿一,雨。為卜臣二章。
廿五。待米而炊,披雨入鎮,二十里淋漓往返,諸事未遂。留卜臣樓頭少話,致印章潤筆,少濟饑渴。
廿六。再入鎮。晨起再為卜臣印章,遂攜付之。
廿九,陰。治諸印璞,竟日為王天章印章,為御周二印章,自欲制用者仍十數方。①從《日記》中我們不難看到鄭?治印的勤奮和生活的艱辛。同時,也得知篆刻藝術在士民階層已經得到普及,印章如同書畫一樣,已經成為一般市民的收藏品。
吳?(1638―?),字仁趾,歙縣人寓居揚州。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其父殘遭兵燹去世。其時吳?年僅8歲,與母避亂金陵,得以幸免于難。母親毀容教養吳? ,親授《漢書》與《孝經》。成年后學詩于吳嘉紀,復移家揚州。詩余習篆刻以治生,頗得時譽,周亮工尤為贊賞,稱吳 “每于兔起鶻落之余,別生光怪,文三橋、何雪漁所未有也”。并說:“予最好雉皋黃濟叔、黃山程穆倩印,兩君年皆近七十,蒼顏皓發,攻苦此道數十年,始臻妙境。而仁趾以英髫之年,遂復及此,其年與濟叔、穆倩齊,其所造當十百兩無疑也。濟叔已矣,同穆倩后先振起廣陵,舍仁趾其誰與歸?”②吳嘉紀亦有詩贊曰:
旅舍沽醪重話故,自言篆學攻朝暮。石上吾初運鐵刀,鐫成人曰如銅鑄。
此藝前推何雪漁,以刀刻石如作書。僻壤窮陬傳姓字,殘章斷跡勝瓊琚。
?也何君同一里,須知助腕有神鬼。手底靈奇甫著名,?城車馬多尋爾。
昨日空囊今有錢,糴糧糴菽上歸船。辛苦高堂頭已白,好憑微技養余年。
①作為書畫家,戴本孝、黃呂、汪士慎、項懷述在篆刻上的貢獻亦不亞于其在書畫上的成就。
戴本孝(1621―1693),字務旃,號鷹阿山樵,前休子,休寧隆阜人,寓和縣。其繪畫擅用 干筆焦墨,意境枯淡,形式簡遠。篆刻以先秦小璽入印,章法、刻法均老道。康熙二年(1663)為冒襄刻有一方六面印,設計獨特,有葫蘆、鐘、方、圓、橢圓等形式,攜帶方便,構思頗具匠心。
黃呂,字次黃,號鳳六山人,歙縣潭渡人。幼承家學,工詩文,精繪事,能書法,擅篆刻。所刻印章遒勁蒼秀,有秦漢遺風。每作畫成,輒題詩幀首,以自所鐫印鈐,人謂之具四美。與汪啟淑交厚,在為汪啟淑刻“天君泰然”印時,邊款題贈絕句一首:
頻年多病萬緣灰,然習雕蟲興未衰。聞說冰斯今再見,特攜新制訪尋來。
門人黃宗鐸“篆刻勁秀入古,論印以章法為本,刀法次之。又手摹印章二帙,幾與印章無別”。②汪士慎(1686 ―1759),字近人,號巢林,休寧人,寓揚州。自幼勤奮好學,多才藝, 詩書畫印都有很高造詣。乾隆四年(1739),左目失明,但心志不衰,寫字作畫,“工妙勝于未瞽時”。并刻有“左盲生”、“尚留一目著花梢”、“晚春老人”、“一生心事為花忙”等閑章,以志其情。篆刻取法小篆,結合漢印結體與章法, 能破能收,自成格局。其章法往往在平穩中求變化,變化中求統一,很有韻味。
項懷述(1718―?),又名述,字惕孜,號別峰,歙縣桂溪人。幼從外舅吳云門學習詩文,吳云門間或自制小印,項懷述亦仿效操刀,不數年即登堂入室,慕名求印者甚眾。后以眼疾,不再刻印。乾隆五年(1740)其父去世,守孝之余,又稍稍從事篆刻,并以示族叔項青來。青來精于篆刻,認為懷述篆刻有功底,勸其輕易不要放棄。懷述遂勤于操刀,直溯秦漢,技益進。不久又以左目看不清停手。乾隆二十四年(1759),“復尋舊業作消遣法,手持三寸鐵,日與片石共語。聞者咸持石索篆,案上石恒滿,閉戶據案奏刀砉然,亦不計其工拙也。”并以所作匯輯成《伊蔚齋印譜》和《黃山印冊》行世。鄭燮為《伊蔚齋印譜》題詞:
追蹤兩漢入先秦,賴古堂中集印 人;?曉風流開下相,波齋穆倩是前身。
同里有項根松、項道?、項綏祖俱精繆篆與繪畫,與項懷述齊名,曹文埴稱之為“南河四項”。
這一階段的篆刻名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還有汪鎬京、王轂、孫克述、吳兆杰、方成培等。
汪鎬京(1634―1702),字宗周、快士,號洋湖居士,歙縣古唐人。安貧樂道,不求仕進。工詩,精于篆刻。著有《紅術軒山水篆冊》4卷、《紅術軒印范》1卷。隨著印章普及和鈐拓的需要,對印泥的質量要求愈來愈高。汪鎬京對印泥進行研究,著有《紅術軒紫泥法定本》1冊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行世。《紅術軒紫泥法定本》分為“砂要染法”、“艾要紅法”、“油要灑法”、“合印色法”、“用印色法”五部分,對如何制作印泥進行了詳細敘述。
王轂,字御菝,號東蓮,黟縣人。少嗜臨池,精鑒賞,訪求周彝秦鼎法帖碑版不遺余力。后從事六書研究,愛好篆刻,經常與吳兆杰、汪肇龍一起,探討六書淵源,切磋刀法急鑿緩鑄之道,章法、刀法深得古意。黟縣現存其“岱峰”石刻手跡。
孫克述(1700―?),字汝明,黟縣人。少有文譽,因科舉不得志,遂究心六書,寄情篆刻。經常至郡城同吳兆杰、汪肇龍、程瑤田、巴廷梅一起討論六書淵源,追蹤秦漢古印。章法、刀法高古渾樸,超絕時流。暇時臨池學書,以晉人為師。梁?對其書法、篆刻作品,極為贊賞,曾寄書獎許。
吳兆杰,字雋千,號漫公,歙縣城里人。幼師從同邑吳天儀學習,通六書,精篆刻。性豪俠、詼諧,治印收入多用于購買法書、古物,亦隨手散盡。乾隆十五年(1750)春,汪啟淑因事歸歙,身體欠佳,閉門謝客。兆杰一日直入寢榻,與啟淑討論印事。汪啟淑《續印人傳》載:
庚午春,予以事牽,歸歙對簿,閉關卻軌,謝絕親朋。而漫公謬信時譽,數叩門欲見。一日直入寢榻前,余方抱疴力疾,與之討論者竟日。漫公以平生無知己,獨許余為賞音。于印章一道,名雖籍籍,然好之者盡如葉公龍耳,惟余識其派別高古,刀法秀雅,迥異時流。相與抵掌歡笑,竟忘憂患中。為余作大小十余印,自具本來面目,頗臻三橋、主臣妙境,絕不類天儀之作。所謂冰寒于水,青出于藍耶!
乾隆二十年(1755)秋當汪啟淑再次歸歙,兩人相見,汪啟淑認為此時的兆杰印作“更蒼老,而各體俱工,于文、何兩君外,另開生面”。①按:“吳士杰”系“吳兆杰”之誤,同書卷四《王轂傳》載王轂“日與漫公吳兆杰、家明經肇隆游”;又民國《歙縣志》卷十《方技》亦記為“吳兆杰,字雋千,號漫谷”。兆杰不僅能刻石,而且還能刻金、玉、晶、牙、瓷、竹,款識尤為精絕。
方成培(1731―?),②字仰松、后巖,號岫云,歙縣橫山人。幼聰慧好學,體弱多病,因此杜絕科舉入仕之念,自學醫道、古詩文、樂律。對詞曲、傳奇方面造詣很深,著有《雷峰塔傳奇》行世。暇時習篆刻,“工程邃一家,極古致磊落,然非賞音、工書畫、佳石舊凍,不屑奏刀”。③同汪啟淑交厚,為其刻印多方,收錄入《飛鴻堂印譜》。有《后巖印譜》行世。
3.徽派篆刻在清代早中期印壇上的主導地位
清初,印壇名手輩出,開始打破徽派一統天下的局面。如林皋崛起于常熟,篆刻古雅清麗,疏密得當,頗有時譽。當時的一些書畫名家王?、惲壽平、吳歷、高士奇、揚晉、徐乾學用印多請他刻。因他原籍福建莆田,故有“莆田派”之稱。許容興于如皋,取法秦漢,篆法工穩,章法疏朗,功力深厚老到。對印學理論頗有建樹,著有《印略》、《印鑒》、《韞光樓印譜》、《谷園印譜》、《說篆》等,人謂之“如皋派之祖”。但是,由于徽派篆刻有程邃、吳? 、項懷述、巴慰祖、汪肇龍、胡唐等領軍人物,在清代早中期印壇上仍占主導地位。
我們先來看看程邃的影響,清初馮泌曾說: 程穆倩名冠南國,以余所見不過數十印,不足概其生平,以所見論之,白文清瘦可愛,刀法沉郁頓挫,無懈可擊,然未脫去摹古跡象也;朱文宗修能而又變其體,近日學者愛慕之。①晚清魏錫曾更說: 程穆倩崛起文、何之后,真豪杰士。余于亂后得其所刻“一身詩酒債,千里水云情”十字印。其遺跡,世間亦頗有存者。己未秋,在荊溪晤王君立齋,得見所藏程譜三百余方,大觀也。穆倩朱勝于白,仿秦諸制,蒼潤淵秀,雖修能、龍泓、完白皆不及,余子無論矣。②魏錫曾精于印學,法眼如炬,他認為朱簡、丁敬、鄧石如都不如程邃,足見程邃在印壇的地位。從清初至現代,很多印人私淑程邃。嘉興俞廷槐,“工摹印,白文宗程穆倩,朱文宗朱修能”。③浙江山陰趙丙?,“摹印初師曙湖,繼學勝代朱修能,后又一變而宗程穆倩,古拙中含蒼秀”。④就是一些開宗立派的大家,也從程邃的印作中汲取營養。如黃易“葆淳”印款記載,“以穆倩篆意,用雪漁刀法,略有漢人氣味”。趙之琛“高頌稿山”印款記載,“次閑為稿山仿穆倩老人”。
吳?與程邃同時而稍晚,篆刻“不規規學步秦漢”,往往把自己對印學的理解滲透到刻印中。周亮工號稱“印癖”,同印人切磋交談,認為“少有當予意者”,但他對吳卻刮目相看,“欣欣嘆觀止”。認為繼程邃后而起的篆刻大家,“舍仁趾其誰與歸”。⑤吳嘉紀也把吳?同何震相提并論,足見其影響之大。
項懷述繼起于乾隆年間,他精于字學,著有《隸字匯》10卷和《隸法匯纂》10卷,對六書有很深的研究,這對他的篆刻是極有幫助的。鮑倚云說:別峰沿波?源,諸體精審,不為贗古,不趨時妍,一澤于雅,而一歸于典。豈惟不為文,何所囿,即櫟下老人與其所稱諸名家,莫之或先矣。①王國棟把項懷述比作程邃:
漢?秦碑自有真,摩挲金石著精神。不工甜美惟中正,此是當年垢道人。②汪秦均則把項懷述當成徽州一脈正燈何震、程邃的繼承人: 吾鄉鐵筆數何、程,前輩風流君嗣興。世上雕搜原不少,何人傳得漢明燈。
③項氏所著的《伊蔚齋印譜》在當時的篆刻界曾引起轟動。
乾隆、嘉慶年間的汪肇龍、巴慰祖、胡唐加上程邃,被世人稱為“歙四子”,是清代早中期徽州印壇上的中堅力量。程邃與汪肇龍、巴慰祖、胡唐三人相距一個世紀,休寧程芝華對這四人特別推崇,精心摹刻四人印作,并匯輯為《古蝸篆居印述》4卷行世。他認為: 新安印人自吾邑何主臣、歙程穆倩后,幾成絕學,汪學博雅川、巴內史晉堂、胡典籍子西繼起,皆力追上乘,討源宿海,得周、秦不傳之秘旨。其兄程芝云亦云:
歙四子之印皆宗秦、漢,汪與巴用高曾之規矩者也,若吾家垢道人,因尸秦、漢,而上稽秦、漢以前金石文字為之祖,而近收宋、元以降趙、吾、文、何為之族,故爐橐百家,變動不可端睨,胡子亦尤此志也。①由于程、汪、巴、胡四人雖名聲較著,但印譜流傳不廣,人們難以見到他們的真跡。程芝華的摹作頗得原作風采,遂使世人賴此書一睹四人風貌,“歙四子”的名號也由此叫響。程邃已作詳細介紹,不贅述。
汪肇龍(1722―1780),原名肇?,字稚川,號松麓,歙縣人。作為一名考據學家,他對字學有著很深的研究。從《飛鴻堂印譜》收錄的他的印作來看,朱文多以小璽及鐘鼎款識入印,秀雅多趣;白文法秦、漢,蒼茫渾厚,印風同程邃接近。
巴慰祖(1744―1793),字雋堂、晉堂,號予籍,又號子安、蓮舫,歙縣漁梁人。巴慰祖是個多面手,無所不好,亦無所不能。家藏法書名畫、金石文字、鐘鼎尊彝很多,工篆隸摹印。喜歡仿制古器物,如舊器一般無二致,雖精于鑒賞者,也無法辨偽。又能作畫,山水花鳥都會,然不耐煩皴染,絕少作畫。篆刻浸淫秦漢印章,旁及鐘鼎款識,功力深厚。晚期印作風貌樸茂古拙,早期印作趨于雅妍細潤、端整純正。汪肇龍、巴慰祖、胡唐三人中,以巴慰祖聲譽最隆,交游也廣。董洵與巴慰祖曾在漢上相聚刻印,互有酬往。晚清趙之謙素以篆刻自負,曾在自用印“趙印之謙”上題“龍泓無此安詳,完白無此精悍”跋語。但他對巴慰祖卻極為心折,“嘗謂近作多類予籍”。②黃賓虹自刻“黃質賓虹”白文印,沙孟海亦稱,“風格逼似巴予籍”。③胡唐(1759 ―1838),④初名長庚,字子西,號?翁,別署城東居士,歙縣城里人。精篆書,善治印,摹秦漢以下至程邃印,皆逼肖入微。印風如其母舅巴慰祖,風格婉約清麗,所著行書邊款尤為精絕。道光七年(1827),程芝華摹刻“歙四子”的《古蝸篆居印述》行世時,胡唐仍在世,并為題“古蝸篆居印述”書名,又作有《古蝸篆居印述序》。程恩澤特別看重胡唐,他在《古蝸篆居印述序》中說:
我歙藝是工者,代有其良。吾宗季子,能作能述,集四賢于一鄉。古蔚若程,古琢若巴,古橫若汪。惟我胡老,能兼三子之長。
從程邃到胡唐,徽州印人沿著追蹤秦漢,從鐘鼎尊彝款識和璽印形式上吸取營養的創作道路上不斷進取,終于趨于成熟,形成風格。
推薦設計

優秀海報設計精選集(8)海報設計2022-09-23

充滿自然光線!32平米精致裝修設計2022-08-14

親愛的圖書館 | VERSE雜誌版版式設計2022-07-11

生活,就該這麼愛!2022天海報設計2022-06-02
最新文章

俄羅斯構成主義的起源藝術理論2006-1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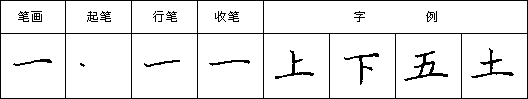
論書法藝術的現代轉型藝術理論2006-11-19

波普藝術(Pop art)藝術理論2006-11-18

書法學習要學會什么?藝術理論2006-11-14